身份的记忆
◎克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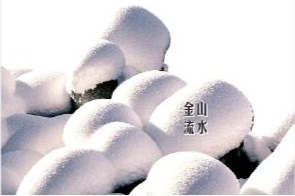
人生在世,总得身负某种身份。有的身份随时间而来,又随时间而去;有的身份既来之则安之,与你不离不弃!有些身份能给你带来快乐,甚至富足;有些身份会给你带来困惑,甚至窘迫!身份像影子,随你而行、虚实相生。当你意识到某个身份不在时,其实,它已经与你结为一体,变成记忆。
今年是我大学毕业40周年,首次同学聚会,因故,一再推迟,直到国庆长假才如大家所愿。梦想成真的那一刻,打了两个多月腹稿的诗作终于“顺产”——
你问,人生最难舍的一段时光
我说,要数元宝山下那三年同窗
喜怒忧思,仿若《元素周期表》一样
课内课外,犹如潮涨潮落的鸭绿江
合唱“再过20年,我们来相会”
等了40年,大家终于兑现了梦想
你眼中的傻小子,他心中的俊姑娘
相聚温泉,谈笑风生,满心欢畅
岁月啊,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
窖藏的酸甜苦辣,变成了佳话和酒香
这首《致同学聚会》的十行诗,我从乌鲁木齐开始构思、在阿勒泰完成初稿、在天津继续改写,直到和同学们围坐在一起举杯同庆的那一刻,才“瓜熟蒂落”。最后一句“窖藏的酸甜苦辣,变成了佳话和酒香”,勾起几位同学对毕业分配的回忆,举杯、碰杯之间,同学们感慨我当初选择去新疆的“决绝”,感叹我“这些年,你真不容易”!
那年8月23日,我怀揣大学毕业生“报到证”和学校给买的“通票”,从丹东出发前往新疆阿勒泰。在北京站办理中转签字后,住进车站附近胡同里3元一晚的小旅舍,然后步行到人民大会堂前拍下人生第一张彩照,又去王府井新华书店买了几本文学书籍。两天后,登上西行的列车,历经四天三夜到达乌鲁木齐。在新华南路干部招待所睡了一夜,第二天一早便乘长途客车出发。又奔波了三天,9月1日下午到达目的地阿勒泰,落脚在骆驼峰下的地区招待所。躺在招待所木头床上的那一刻,我似乎有了点“到家”的感觉。千里迢迢的长途旅客身份不辞而别了,只剩下待分配的“大学毕业生”一个身份。那张被折成小方块的“报到证”,既是我们的身份证明,也是我们的“护身符”,在关键时刻能帮我们“排忧解难”。傍晚时,地区教育处副处长邹飚得知分配到阿勒泰的两位大学生已经到了,便来到招待所看望,询问我们旅途情况和饮食习惯,并一再嘱咐:“明天一早去地区教育处听候组织分配。”
第二天早上,我和同伴带着“报到证”来到行署大楼一楼教育处,领导们碰过头后,将我分配到地区二中教化学,同行的中文系校友留在教育处搞职工教育。听到没把我们往县上分配,我心里才踏实了。至此,陪伴我们一路的“报到证”也挥手告别,进入了档案袋。而千里迢迢跟随我们的“大学毕业生”身份也完成使命,成为周围的一时话题和个人的终身记忆。
等了一会儿,二中派来一台小四轮拖拉机,刘师傅接上我们去拉行李,然后“突突突”地开到了二中校园。在宿舍简单安顿好行李后,我立刻去教学楼三楼校长室报到。随后,教务处的杨主任带我来到一楼化学教研组。组长周老师和几位女教师热忱欢迎我的到来,腾好的办公桌上放着教科书、备课本、文具和一张油印的《课程表》。当我坐在办公桌前,“化学教师”的身份似乎恭候已久,终于相见。第二天上午,便走上讲台,开启了我教师生涯的第一堂化学课。
春季开学后,新增的一个毕业班化学课,强化了我的化学老师身份。四月中旬的一天,李校长口头通知,安排我去乌鲁木齐参加自治区优秀大学毕业生联谊会。我乘坐长途班车跑了三天,提前到会。来自南北疆各地的大学毕业生代表有上百人,大家聚集在光明路博格达宾馆。已经成为档案的“大学毕业生”身份,在那一天又回到青春洋溢的脸上。一批受到表彰的“优秀大学毕业生”上台领奖,激昂的发言不时引来掌声。会餐期间,有关“西部开发”的倡议成为热议话题,一曲《风雨兼程》引得大家群情激昂、挥泪共唱。会下交流时得知,那两年,分配到阿勒泰地区的外地大学毕业生只有两批,总共7人。联谊会结束后,我带上新买的几本诗集和会上发的“优秀大学毕业生奖状”,再次踏上奔向阿勒泰的旅程。三天后回到学校宿舍,“大学毕业生”“旅客”的身份再次不辞而别,剩下“化学教师”的身份,陪伴我课堂内外整整八个春夏秋冬,一直持续到1993年初冬,女儿已经三岁半了!

















